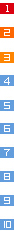難忘那年五月初三
| 2025-06-06 11:21:57? ? 來源: 集美報 責任編輯: 李霖 我來說兩句 |
分享到:
|
斑駁的紅磚墻像一本翻卷了邊的舊書,在歲月的風里沙沙作響。“五月初三” 四個粉筆字歪斜著,像跌跌撞撞的孩子,深深嵌進磚縫,也嵌進了我記憶的最深處。那是母親走后的第三天,大妹踮著腳尖,小手顫抖著寫下的。粉筆灰簌簌落下,如同紛紛揚揚的雪,落進磚縫,也落進了我們破碎的心。四十年過去,每當我閉上眼,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指尖拂過磚面時的粗糲,仿佛又回到了那個悲痛的清晨。 我的童年,沒有五彩斑斕的玩具,沒有嶄新漂亮的衣裳,只有與母親相依為命的每一個日夜。家里七個孩子,母親就像永不停歇的陀螺,在生活的漩渦里打轉。白天,她在生產隊里拼盡全力掙工分,汗水濕透了衣衫,在烈日下結出白色的鹽霜;夜晚,她就著昏黃搖曳的煤油燈,一針一線地縫補衣裳,那跳動的火苗將她疲憊的身影拉得很長很長。她的咳嗽聲,成了我童年揮之不去的背景音,從輕微的慢性支氣管炎,漸漸發展成了嚴重的肺心病。每到深夜,那一陣接著一陣的咳嗽聲,就像一把把鈍刀,一下下地割著我的心,讓我輾轉難眠。 最刻骨銘心的,是給母親刮痧的情景。由于窮得請不起大夫,母親就把希望寄托在這土法子上。她讓我用那把豁了口的瓷湯匙刮她的背,聲音沙啞卻堅定:“使點勁,刮透了才管用。” 瓷湯匙緩緩劃過她瘦弱的脊背,紫紅色的瘀斑漸漸浮現,像天邊絢爛卻轉瞬即逝的晚霞。我的手顫抖得厲害,生怕用力過猛弄疼了她,可母親反手緊緊抓住我的手腕,狠狠往下按。夜里,萬籟俱寂,我聽見隔壁傳來壓抑的啜泣聲,那聲音如同一根根銀針,扎進我的心里。我把臉深深埋進枕頭,淚水洶涌而出,浸濕了粗糙的稻草芯子。 母親教給我的,遠不止生活的艱辛。還記得那些做酒曲的日子,她帶著我蹲在郁郁蔥蔥的菜地里,精心挑選辣蓼草。她的手指沾滿黃綠色的草汁,散發著獨特的清香。我們把米粉和老曲仔細地拌成面團,母親總會用指尖輕輕挑出一點,笑著遞到我嘴邊,讓我嘗嘗。那微酸帶甜的滋味,至今仍縈繞在舌尖,仿佛從未消散。做好的酒曲拿到集市上,五分錢一個,換來的作業本上,還留著她勞作時留下的淺淺指印,那是母愛的印記。 獨眼的李婆婆來借油時,母親總是毫不吝嗇。她把油勺刮得干干凈凈,滿滿舀上一碗,最后還用食指小心翼翼地將掛在碗沿的油珠抹進碗里。我噘著嘴,滿臉不樂意,母親就用帶著菜油香的手,輕輕摸著我的頭,語重心長地說:“三兒,餓肚子的滋味,嘗過就忘不掉。誰還沒個難處?鄉里鄉親的,幫人就是幫自己。” 這些話,如同一顆種子,深深埋進了我的心里。后來我成為一名醫生,總會給貧困患者帶上一份熱乎乎的盒飯,就像母親當年幫助李婆婆那樣。 夏天澆菜,是我最快樂的時光。小木桶里盛滿清涼的水,我蹦蹦跳跳地走在田埂上,木桶隨著腳步晃蕩,濺出的水花在陽光下閃爍著光芒,在身后留下一串濕漉漉的腳印。母親站在菜畦邊,臉上掛著溫柔的笑容,豆大的汗珠順著她瘦削的下巴滾落,滴進肥沃的土地。茄子花在陽光的照耀下,泛著淡雅的紫色,像一個個小燈籠;螞蟻排著隊,順著藤蔓慢悠悠地往上爬。這些畫面,就像一幅幅畫卷,鮮活地保存在我的腦海中。 母親離開那年,我才13歲。她沒能等到我初中畢業,沒能看到我考上心心念念的衛生學校,更沒能穿上我用第一筆工資買的的確良襯衫。但那些土窯燒制的紅磚,記錄著我們生活的艱辛;她親手編織的竹籃,盛滿了我們的希望;下雨天叮咚作響的水缸,訴說著歲月的故事……它們都在替我銘記,那個用瘦弱多病的身軀為我們遮風擋雨,撐起整個童年的偉大母親。 如今,孩子們的兒童節,總是充滿了彩帶的絢麗和糖果的甜蜜。而我的童年記憶,永遠停留在五月初三的清晨。在母親用舊瓷勺刮痧的聲響里,在她編竹籃時指尖翻飛的塑料帶上,在那些與她共度的點點滴滴中。這些記憶,就像老屋墻上的粉筆字,即便磚塊早已被歲月風化,字跡卻一年比一年深刻,永遠鐫刻在我的生命里。 (來源:集美報) |
相關閱讀:
 |
打印 | 收藏 | 發給好友 【字號 大 中 小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