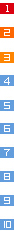花雨深處萱草情
| 2025-05-21 10:57:47? ? 來源: 集美報 責任編輯: 李霖 我來說兩句 |
分享到:
|
五月的風掠過院墻,檐角垂下的薔薇花便簌簌地抖落幾片胭脂。我站在老槐樹斑駁的影子里,看母親踮腳晾曬新漿的被單,她的銀發在暮春的光線里泛起溫柔的漣漪。樓下雜貨鋪新進的康乃馨開始漲價,日歷上的紅圈圈一天天逼近,我卻總覺得那些精心包裝的花束,遠不如母親圍裙口袋里永遠揣著的手絹真實。 前些日子在公園遇見奇景。一只灰喜鵲銜著肥碩的青蟲,被三只嘰喳的幼鳥追著掠過紫藤架。雛鳥的絨羽尚未褪盡,卻已懂得張開嫩黃的喙。鳥媽媽忽而急轉停駐在冬青叢中,將食物塞進某個孩子的嘴里,又匆忙飛向更遠的香樟樹——原來是在教孩子們辨認安全的覓食點。這讓我想起童年每個暮色四合的黃昏,母親總要把晾在竹竿上的衣裳一件件摸過去,確認徹底干透了才收回衣柜。 老式縫紉機的嗒嗒聲是記憶里永恒的背景音。母親踩著鑄鐵踏板,讓細密的針腳在布料上流淌成河。她總能把哥哥磨破的褲膝補成帆船的模樣,將我的碎花裙接上新蕾絲邊。去年收拾舊物,翻出件我小學時的棉布罩衫,褪色的補丁處竟用白線繡著朵小小的鈴蘭——三十年前的秘密,在五月的陽光下突然綻放。 母親的手掌紋路里嵌著永遠洗不凈的蔥蒜氣息。那雙手能同時攪動鍋鏟與電話聽筒,在油煙里解答我幼稚的十萬個為什么。最難忘中考前夜突發高燒,她整宿用酒精棉球擦拭我的掌心,冰涼的觸感每隔十分鐘準時落下,比床頭的小鬧鐘更精確。晨光初露時我退燒了,她卻帶著滿眼血絲鉆進廚房熬粥,案板上的皮蛋被她切得如月牙般瑩潤。 去年深秋陪母親回湖南老家,見她蹲在祖宅后的菜畦邊久久不動。順著她的目光望去,幾株經霜的卷心菜正在抽薹,青紫色的花莖倔強地刺向天空。“你外婆總說,菜若留到最后不收割,就會拼死開出花來。”母親輕輕觸碰那些即將凋謝的花苞,像是撫摸時光那頭的另一個母親。我突然驚覺,那些被我們歌頌的犧牲與奉獻,或許不過是生命延續的本能,如同卷心菜用最后的力氣綻放,只為讓種子乘著南風遠行。 前日幫母親染發時,發現她耳后新添了塊老年斑。她反倒笑著指給我看窗前的水仙:“你爸養的這盆倒是精神,球莖都裂成七八瓣了,每個小芽還拼命往外鉆。”暮春的雨絲斜斜掠過玻璃,將那些奮力舒展的新綠洇成朦朧的水墨。母親的白發在染發劑作用下漸漸轉深,仿佛歲月倒流,而我知道這只是暫時的魔法。 樓下面包房開始售賣母親節蛋糕,奶油堆砌的康乃馨在櫥窗里永不凋謝。可我記得真正的母親花是萱草,古代游子遠行前要在北堂種下忘憂草,而我的北堂始終是廚房里飄著蔥花香的方寸之地。此刻母親正在教孫女包薺菜餛飩,一老一少的笑聲驚動了窗臺上的麻雀,撲棱棱飛向綴滿槐花的枝頭——那些米白的花串多像綴滿時光的瓔珞,每一粒花苞都蓄著整個春天的乳液。 暮色漫上來時,母親照例要去澆她種在泡沫箱里的小蔥。塑料噴壺在她手中劃出銀色弧線,細密的水霧間忽然架起七彩虹橋。我想起二十年前她也是這樣澆灌我的童年,那時總覺得母親是口永不干涸的井,如今才明白她只是把生命擰成了滋潤萬物的甘霖。此刻風起,滿樹槐花落如碎雪,而母親站在紛紛揚揚的花雨里,成了春天最深情的注腳。 (來源:集美報) |
相關閱讀:
 |
打印 | 收藏 | 發給好友 【字號 大 中 小】 |